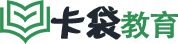以诗为词的诗人是谁(怎样评价苏轼的以诗为词)

苏词最主要的创作特色是什么呢?历来的作家和批评家都异口同声地回答说,是以诗为词。《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二引《王直方诗话》载晁补之、张耒云:(东坡)先生小词似诗。
贬之者如:
陈师道《后山诗话》云:
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
《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引李清照云:
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耳。又往往不协音律。
褒之者云:
王灼《碧鸡漫志》卷二:
东坡先生以文章余事作诗,溢而作词曲,高处出神入天,平处尚临镜笑春,不顾侪辈。或曰:“长短句中诗也。”为此论者,乃是遭柳永野狐涎之毒。诗与乐府同出,岂当分异?
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今少年妄谓东坡移诗律作长短句,十有八九不学柳耆卿则学曹元宠,虽可笑,亦毋用笑也。
刘熙载《艺概》卷四云:
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若其豪放之致,则时与太白为近。
上举这些大家所熟知的材料提供了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那就是:无论他们对于苏轼以诗为词所采取的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但意识到这一点是苏词主要的创作特色,却是共同的。肯定了这一点,我们就很自然地要提出两个问题。其一,人们根据什么理由在苏词的许多创作特色之中,突出这一点来加以注意和褒贬呢?其二,所谓以诗为词,又包含了一些什么具体涵义呢?关于前者,可以从对于词史的溯溯上得到解释。关于后者,苏词本身就可以给人们作出确切的说明。
词,本来是唐代人民群众所创造的一种新的音乐歌词。和其它样式的民歌一样,它必然地会广泛地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反映当时人民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情况和愿望,当然其中也包括了男女爱情方面。现存敦煌卷子中的作品,虽然为数不多,但是大体上也可以看出其中消息。作家们,无论他们是自觉还是不自觉,总是要向民间的新兴文学样式学习,并在其中吸取养料的。这,实质上也就是由民间词上升为文人词的历史过程。这种学习,虽始于中唐,但到晚唐、五代才获得较大的发展。由于当时政治混乱,社会黑暗,多数作家们的精神状态都陷入颓废空虚;加以某些地区(如黄巢起义以前的长安以及十国中的西蜀、南唐)暂时苟安的政治局面和畸形发展的都市繁荣,又为这些作家(特别是一些上层的贵族,如《花间集》中某些词人和南唐二主、冯延巳等)提供了享乐的条件,因而在他们通过其创作实践来发展和提高这种音乐歌词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按照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美学趣味片面地突出了其中有关男欢女爱、别恨离愁的部分。这就使得这种样式,本来和其它样式一样,可以反映广阔的生活面的,变得反映的范围相当狭窄,似乎词只能是剪红刻翠的“艳科”,或者旖旎温柔的“情语”了。从温庭筠到柳永,这种“艳科”、“情语”,在词中,竟成为普遍的和最有势力的题材和主题。作家们在填词的时候,几乎完全排斥了,甚而至于认为应当排斥广阔的生活画面和比较重大、严肃的内容,否则就要被认为不合色,不当行。在这一段时期中,如李珣、孙光宪对风土的歌咏,鹿虔扆、李煜对故国的哀思,范仲淹写塞上风光,柳永写都市繁华,对多数词人们所拘守的狭窄范围有所突破,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但没有能够改变它总的倾向。直到苏轼,以诗为词,才比较彻底地打破了这个相当悠久的,但并非健康和合理的传统,使读者、歌者和其他作者一新耳目。这自然不能不算是一项重大的革新,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它还意味着恢复了民间词无论从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段上都能够比较广阔地反映生活的那种古老而优良的传统。试想,这怎么能够不成为词坛上令人十分重视和关切的事态呢?
现在,可以进一步探索一下以诗为词的具体涵义究竟是什么?
以诗为词,首先指的是词所反映的生活内容的扩大。苏词中所描写的情事,当然有许多是和其以前的词人相同的。但是,许多被别人认为不适宜于用词来描写的情事,苏轼也毫无顾忌地将其写入词中来,诸如人生的感慨、仕途的升沉、交游的聚散、州邑的去留、自然景物的欣赏、农村生活的写照,甚至打猎、参禅等等,都是前人词中反映较少或完全没有涉及的。另外,在少数篇章中,他还隐约其辞地表现了自己的社会政治观点和对于时政的看法,虽然这一方面还发展得不够充分。总的说来,苏词中一些题材和主题,是从温庭筠以来的词人的作品中所找不到的,但却是前代诗人的作品中所常见的。刘熙载说,苏词“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可能还不能完全落实,然而这位批评家所指出的苏轼以诗为词的具体涵义的一个方面,显然是正确的。
被苏轼所扩大了的词的内容,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艺术手段,首先是语言。因此,以诗为词的具体涵义,就不能不将以诗的语言来写词这个概念包含在内。如果我们细加辨别,就可以发现,这还不止是一般地以诗的语言来写词的问题,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还是以有别于唐诗语言的宋诗语言来写词的问题。宋代诗人如欧阳修、王安石等已有意识地从唐代大师杜甫、韩愈等的语言宝库中吸取了自己所需要的营养,从而形成了宋诗语言的特色。苏轼也正是积极参预了这一艺术活动的人。这样,在他从事词的革新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或者说很自然地将诗的语言,特别是宋诗的语言带进了词里,从而形成了炫烂多彩的风格。例如,雄壮超脱的则有〔念奴娇〕(“大江东去”)、〔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清新明快的则有[贺新郎](“乳燕飞华屋”)、〔洞仙歌〕(“冰肌玉骨”)等,奔放流转的则有(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水调歌头](“落日绣帘卷”)等,沉挚深永的则有〔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范茫”)、[永遇乐](“明月如霜”)等。此外,如[哨遍](“为米折腰”)、[满庭芳](“归去来兮”)等,则已经高度散文化;[减字木兰花](“贤哉令尹”)、〔无愁可解〕(“光景百年”)等,更出之以议论;[如梦令](“水垢何曾相受”、“自净方能净彼”)、[南歌子](“师唱谁家曲”)等,又加之以俗语、禅语。这一切,都是由于适应词的内容的扩大而形成的语言特色,并从而直接构造了苏词的独特风格。将这些作品和前人的诗和词分别加以比较,就可以发现,它的语言和风格,是更其接近于前人的诗(和苏轼自己的诗)而远于前人的词的。在《文说》中,苏轼将自己的文章描写为:“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这位艺术巨匠以水之能“随物赋形”来比喻他运用语言的本领,是合适的。他创造性地使用诗的语言来写词,为他所扩大的词的内容找到与之十分相适应的形式,也足以证明他自我评价的正确。
勇敢地将词写成如李清照所讥讽的“不协音律”的“句读不葺之诗”,乃是苏轼以诗为词的又一具体涵义。前人曾将这一点归咎于苏轼不通词乐,不善唱曲。但根据有关这个问题的现存全部材料看来,陆游在其《老学庵笔记》卷五中所说的“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这个结论还是下得对的。由于苏轼在其创作实践中并不十分严格地拘守声律成规,就使得词从他开始,更其明确地不仅以音乐歌词的身分存在于艺苑,而且以抒情诗的身分出现于诗坛。在其后词乐逐渐消亡的过程中,词终于脱离了音乐,成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样式,而依然存在下去。从元、明以来,直到现在,还有人用这种样式来进行创作。所以苏词不剪裁以就声律,从音乐和歌唱的角度看来,在当时也许是不怎么妥当的;但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说,则是一种当内容与形式发生矛盾的时候,宁肯使内容突破形式,而不肯使形式束缚内容的正确方法。这不仅对当时的创作风气起了良好的推动作用,而且对于词之成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样式也起了不可抹杀的支持作用。我们在估计苏词的历史功绩时,似乎不应当把这一点除外。
综上所说,苏轼以诗为词的积极意义就在于改变了词的传统,扩大了词的内容,丰富了词的语言和风格,并且为词发展成为独立的抒情诗样式准备了条件。
相关问答
-
儒家的“中庸”之道是否适用于当代

普通人理解的中庸之道,就是凡事求中。“中”就是不偏不倚,不左不右,不激进也不保守,徇中道而行。这种行为方式很容易被批评为“庸”,因
阅读更多 -
如何用一句话来概括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是传播普世价值的文化-就是人类都应该遵守最基本的价值原则。儒家文化的中心思想是仁义道德。而仁义道德也是围绕着仁展
阅读更多 -
道家的文化是世人追求的养生之道和避世之谈吗?

“道家文化”在历代圣贤美德的不断进化发展下,道家文化相互汲取营养,当然不仅仅包括如何养生修行于世,万物的本源是“道",无论做什么,都
阅读更多 -
黄老之学跟道教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没有被延续?

黄老之学,始于战国盛于西汉,“黄”指传说中的黄帝;“老”指春秋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黄老”即是二人的合称。战国末期,诸子百家思
阅读更多 -
庄子思想给我们的启示

庄子,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奇人。他的文章、思想、生活态度,别具一格,与众不同。当然,庄子思想奇特之处,主要相对于传统儒家思想。因为儒家
阅读更多 -
春秋战国为什么法家能脱颖而出?

法家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研究国家治理方式的学派,提出了富国强兵和依法治国的思想。它是诸子百家之一,是战国时期主张以法治为核心思想
阅读更多
最新问答
-

儒家的“中庸”之道是否适用于当代
2024-05-19 -

如何用一句话来概括儒家文化?
2024-05-19 -

道家的文化是世人追求的养生之道和避世之谈吗?
2024-05-19 -

黄老之学跟道教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没有被延续?
2024-05-19 -

庄子思想给我们的启示
2024-05-19 -

春秋战国为什么法家能脱颖而出?
2024-05-19 -

儒家的经典三礼
2024-05-19 -

庄子的隐逸态度是消极思想还是积极思想?
2024-05-19 -

生死轮回是自然过程,那么庄子对待生死的观点又是什么?
2024-05-19 -

韩非子“法”“术”“势”三大思想精髓
2024-05-19